
“我们在拒绝过去,拒绝被约束,拒绝成为我们母亲那样的人。就好像长居内陆的整个民族爬上了悬崖,第一次看见了辽阔无垠的大海……一切皆有可能。”

“不能游行的人选择写作。”
2021年,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她们合著新作《依然疯狂》的开篇这样写道。
女性主义的道路上,所有女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参与,不被落下。通过这些书籍,你能听见她们正在释放被压抑的声音,疯狂呐喊,整耳欲聋。
用文字向每个女孩传递力量,一起见证关于女性的所有可能!
“我们也很困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我们依然疯狂”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
《依然疯狂》


为什么我们和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依然疯狂?这里的疯狂是一种愤怒,是一种被激怒、感到困惑,并渴望反抗的情绪。或许你走了很远之后,会遇到防守方的反击。或许你在打破玻璃天花板之后,会被迫在碎玻璃上行走。或许你在主动出击的过程中会摔倒。

性别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它最终的整体形式永远地被延宕,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它都不是它的真实全貌。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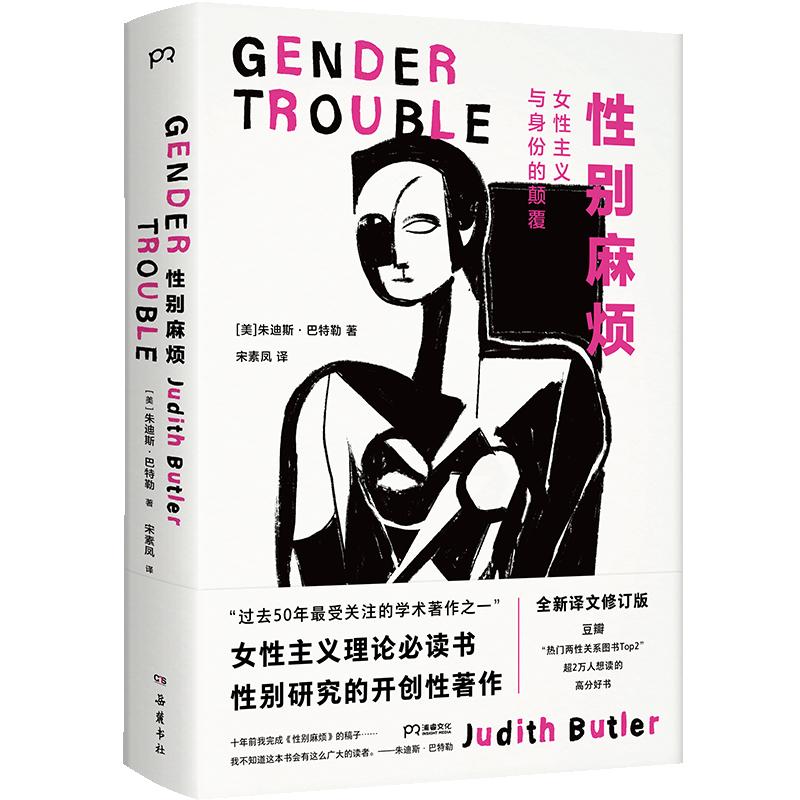

我试图对抗那些对性别的界限和适当性作一些自以为是的假定,并把性别限定于一般所接受的男性与女性的概念的观点。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任何以其实践先决条件为由而限制性别意义的女性主义理论,都在女性主义内部设立了排除性的性别规范,而且往往带有恐同症的后果。过去对我来说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女性主义应该小心不要理想化某些性别表达,这将反过来产生新的等级与排除的形式。特别是,我反对那些真理体制(regimes of truth),反对它们规定某些形式的性别表达是错误的或后天衍生的,而另一些则是正确的和原初自然的。重点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性别化的生活方式,以为本文的读者提供一个可能的典范。相反地,本文的目的是想为性别打开可能性的领域,而不强制规定什么形式的可能性应该被实现

“假如妇女住在和男人很不同的国度,从来没有读过男人写的任何作品,那么她们将会拥有自己的文学。”
伊莱恩·肖瓦尔特
《她们自己的文学》


19 世纪女作家对同时代的人来说首先是女人,其次才是作家。一个女小说家如果不用男性笔名伪装,必料定评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女性身份上,并把她与当时的其他女作家归为一类,无论她们的题材和风格有多大的不同。个人的成就总会被放在相形见绌的刻板组合之中,这样的认识始终刺激着女性小说家。乔治·爱略特反对有人把她比作黛娜·马洛克;夏洛特·勃朗特推迟发表《维莱特》(Villette),为的是可以不同盖斯凯尔夫人的《露丝》被放在一起评论。勃朗特尤其希望阻止男性文学权势把女作家变成争夺同一块小地盘的竞争者和对手。“妒忌是作家的本性”,她给盖斯凯尔夫人的信中写道,但是“我们就是不听他们的;他们不可以把我们变成敌人”。

“生命并没有那么重要,艾伦。”我说,“除了恶劣的日子、糟糕的男人,我们一无所有。”
格蕾丝·佩雷《最后一刻的巨变》


在我们暗无天日的地下公寓,在黑漆漆的一天,一个父亲猛地坐进宽大的椅子里,等着领他的两个孩子回家, 那两个孩子是我孩子的朋友。就在带孩子离开前,他看向了我。他说他的前妻,也就是孩子们的母亲,我的朋友蒂比,要他读读我写的故事。我很可能说的是:哦,你别放在心上。但他确实放在心上了。两星期后,他又来接孩子们。这一次,他坐在了厨房的桌边(在房间里边充当待客的桌子)。他问我是否可以再写七篇小说,和他读过的那三篇类似就行。他说他要出版这本书,将由双日出版社出版。他叫肯·麦考密克,是个编辑,因此可以说这样的话,并且一定能实现。
自从写了《人的小小烦恼》,我就经常离开家。作为和平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我通过政治工作有了巨大收获。在战争期间,我带着政治任务游历越南,也去了瑞典、俄国、中美洲,看见了中国、智利,并在会议上进行了汇报。因此,在《最后一刻的巨变》和《当天晚些时候》这两本书中,与我同在的一些人不得不和我分享这些旅程。当然了,有些人仍旧很年轻,他们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
其中许多人依然是我的好伙伴,构成了我巨大的好运。有我孩童时期的邻居,有我孩子们小时候的邻居,在儿童的公园或是大人的五角大楼边发生的示威中,在生机勃勃的邻近街区反对海湾战争的游行中,在与我们自身及他人的激烈对抗中,我们保持了对文学和世界的兴趣与积极性,现如今,我们正携手老去。

女性主义是不同年龄的女性,站在各种立场上创造出来的一股汹涌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巨浪。
上野千鹤子《女性主义40年》


对于“这样的社会”,女性早已给出了答案——非婚化与少子化。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生不了,养育不了。女性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就是历史给出的答案。针对家庭危机问题,守旧势力试图用社会性别抨击的方式反击,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呼吁“守护家庭”的声音越高,新自由主义强加于女性的“自我责任”重担就会越发导致家庭的崩溃。
女性主义终将与新自由主义割袍断义,这样才能逐渐分清女性阵营中的敌与友。治疗方法已然详尽,处方已然反复斟酌,方案已然提出。
我们需要的社会,是任何人在任何年龄都可以重新来过的社会;是可以自由选择劳动方式且不受区别对待的社会;是女性能够自由选择育儿或照顾老人,不受强制、不孤立无援、不因这种选择而蒙受损失的社会;是女性不会受到男性暴力或性骚扰的社会;是女性即使孤身一人也能安心生育孩子的社会。
正因为这些方案一个都没有实现,女性主义的历史责任仍将不断继续。

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我希望追溯五名女性的足迹,在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她们的经历,并沿着她们的道路穿越阴霾和光明。她们的价值远不止我们以为的那几具空荡荡的人类躯壳:她们是哭着要妈妈的孩子;她们是坠入爱河的姑娘;她们经历过分娩之痛和双亲的死亡;她们欢笑着庆祝圣诞的到来。她们与兄弟姐妹争吵,她们流泪,她们怀揣梦想,她们受伤,她们享受微小的胜利。她们的人生轨迹是维多利亚时代众多女性一生的缩影,而她们的结局又是如此异乎寻常。正是为了她们,我才写下这本书。我之所以提起笔做,是希望如今的我们现在可以听清她们的故事,并将那些一度从她们的生命中被残酷夺走的东西交还给她们——那就是尊严。

我捍卫女性权利,是因为她们与我平等,是因为女性权利就是人权,此外,我对人类同胞遭受的暴力感到愤慨。我们必须共同为女性而战。
德尼·穆奎格《女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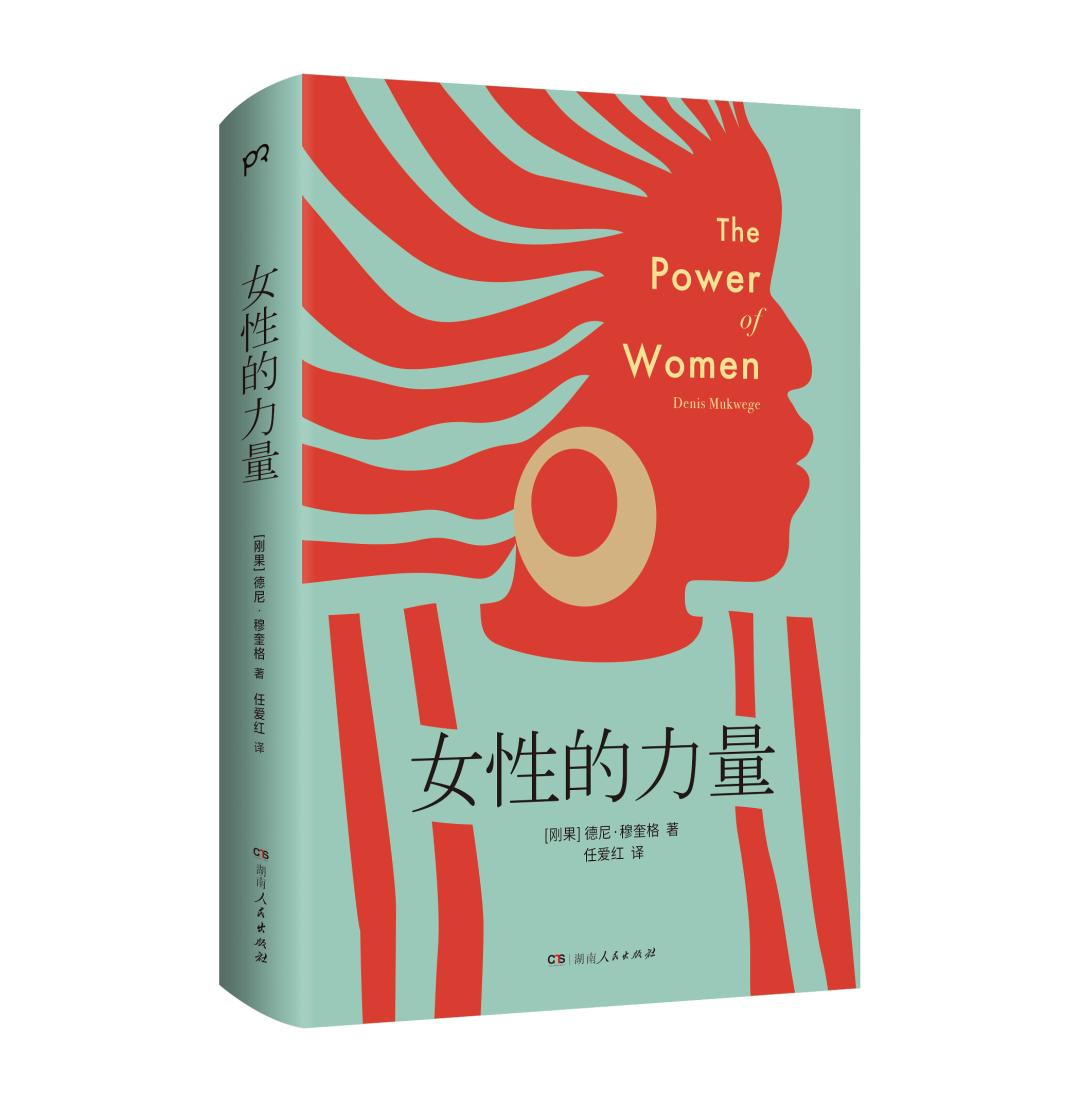

虽然这主要是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但它不仅仅是为女性而写。我热切希望所有性别的人都来阅读这本书,从中学习。我们需要更积极地参与争取两性平等的斗争。男人们站出来支持他们的姐妹、女儿、妻子、母亲、朋友和人类同胞时,不应该害怕不被他人理解,也不应该像我以前那样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辩解。
单凭女性自己无法解决性暴力问题;男性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连接着婴儿与母亲的脐带会被某个无关的人剪断,肚脐作为脐带存在过的痕迹,寂寞地留在人体的中央。
宇佐见铃《我想生下妈妈》


对性行为抱有抵触心理,这在青春期是很常见的吧,可小兔无论怎么成长,都无法摆脱这种抗拒。我就是无法接受。婴儿与母亲的相遇为什么必须经历那种过程?为什么小兔只能通过剥夺卡卡的处女身才能遇见卡卡呢?
小兔想用不伤害卡卡的方式遇见她,仅仅是为此,小兔想怀上卡卡。
等待着我们的未来,虽然寂寞却也稀松平常,谁也不会为此悲伤吧。自然也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悯吧。毕竟大家都很寂寞。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而寂寞。既然没有神明为我们寂寞,就由小兔来成为我们的神明吧。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救赎了。

你不必独自站在那里;你和我们所有人站在一起,我们彼此扶持,要求正义。
玛莎·努斯鲍姆《傲慢的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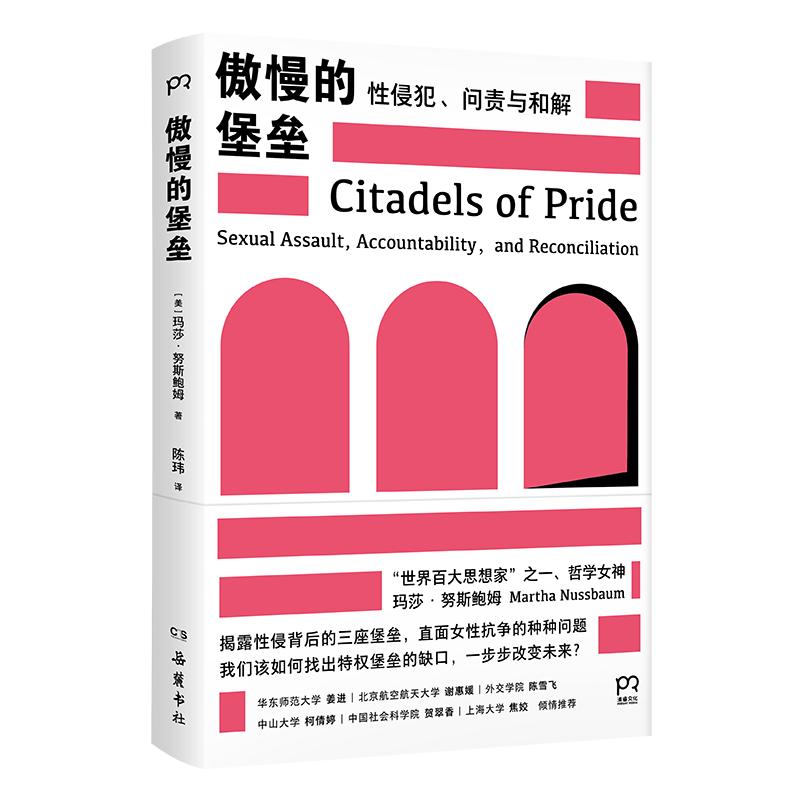

#MeToo 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也令公众意识到对女性造成的这些特殊伤害具有普遍性,意识到它们所造成的严重不良影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场运动绝不是由那些有名望的吹哨人一手促成的。普通女性和她们的律师数十年来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的努力在塑造一种法律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在这种文化中,女性的指控可以得到认真的对待,即使她们并不总是胜诉。大量增加的声音已经开始创造一种自信的文化:如果这些勇敢的女性不畏惧地站出来,如果众多女性都做出了理性的推断,那么我也应该愿意说出真相。#MeToo 运动的整个理念就是一种在问责方面要求团结的理念。#MeToo(“我也是”)这个标签向女性提供了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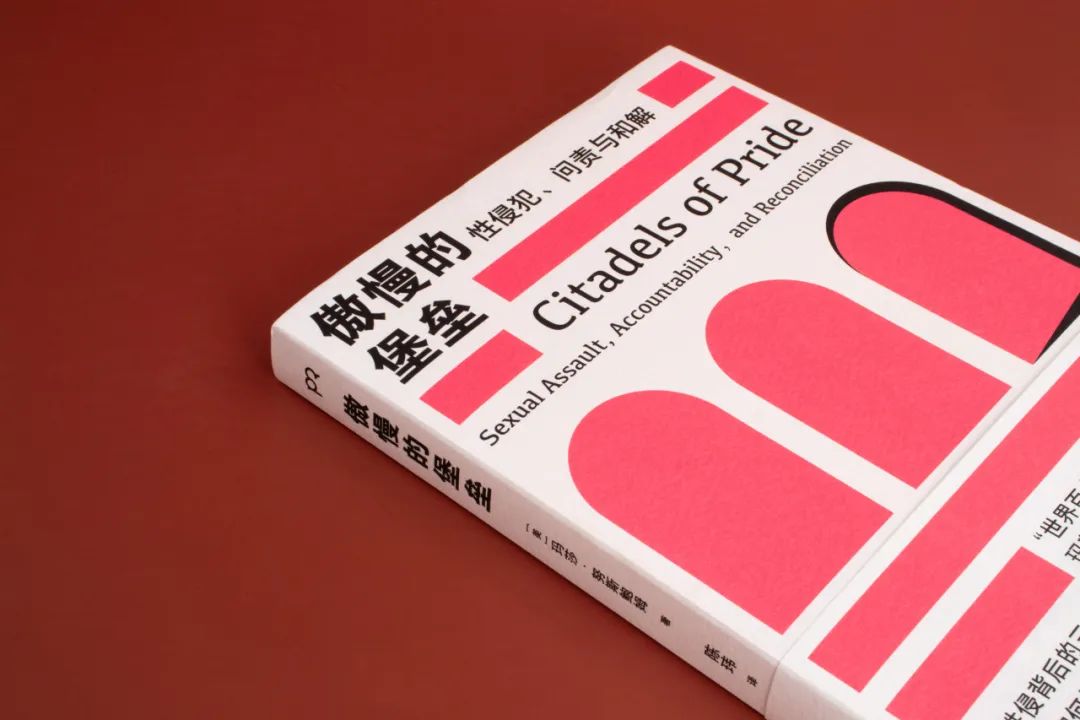
面对生活,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除了写作。
德博拉·利维《我不想知道的事》
一个女人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在世界中获得一个小角色?
德博拉·利维《生活的代价》
家庭空间,不过是女性在借用的空间。
德博拉·利维《自己的房子》


母亲是全世界都极力想象的那个女人。世界对我们活着的意义抱有充满怀旧色彩的想象,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也怀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想象,规定了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且极力想符合那些要求,为此吃尽苦头。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社会系统想象出来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母亲”其实是一种妄想,世界爱这一妄想超过爱母亲本身。尽管如此,揭穿这个妄想还是让我们感到内疚,担心我们为自己和心爱的孩子所造的壁龛,会坍塌在我们沾满泥水的运动鞋旁——这鞋子可能是在遍布全球的血汗工厂里,由可怜的童工缝制的。这情况有些难以理解,因为在我看来,男性世界及其政治格局(从不利于儿童和女性)实际上是在嫉妒我们对婴孩浓厚的爱。和一切与爱有关的事物一样,孩子让我们感到极其幸福;当然,孩子有时也会让我们难过,但从不会像二十一世纪的新男权政治这样让我们备受折磨。它要求我们既被动又有雄心,既有母性的慈爱又要保持旺盛的性欲,既要无私付出又要感到满足——我们要成为无所不能的现代女性,同时还得承受经济和家庭方面的种种羞辱。如果说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在为这样那样的事而感到内疚,但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一片阴沉的现代家庭政治已变得复杂又混乱。我认识许多影响力强大的现代女性,她们为他人打造了一个家,自己身在其中却没有家的感觉。她们更喜欢办公室或其他任何工作场所,因为在那里她们拥有比“妻子”更高的地位。奥威尔在 1936 年写成的文章《射象》中指出,帝国主义者“戴着面具,脸渐渐长成了面具的样子”。妻子也戴着面具,脸也会长成式样各异的面具的样子。有些女人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却因取得了成功而受到丈夫暗地里施加的惩罚。她们的丈夫变得怨天尤人,怒火中烧,垂头丧气。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告诉我们的,在这个成功和权力为男人而设的世界里,女人不该让男人黯然失色。如果在经济上仰赖于女性的才干,男人就必然难以施展支配女性的历史特权(虽然这种特权已有了现代转向)。同时,她获得一条灾难性的启示:她必须隐瞒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才能得到他的爱。他们都知道,两人必须共同维护一个谎言,好挽救他的颜面,而他的脸也在渐渐长成面具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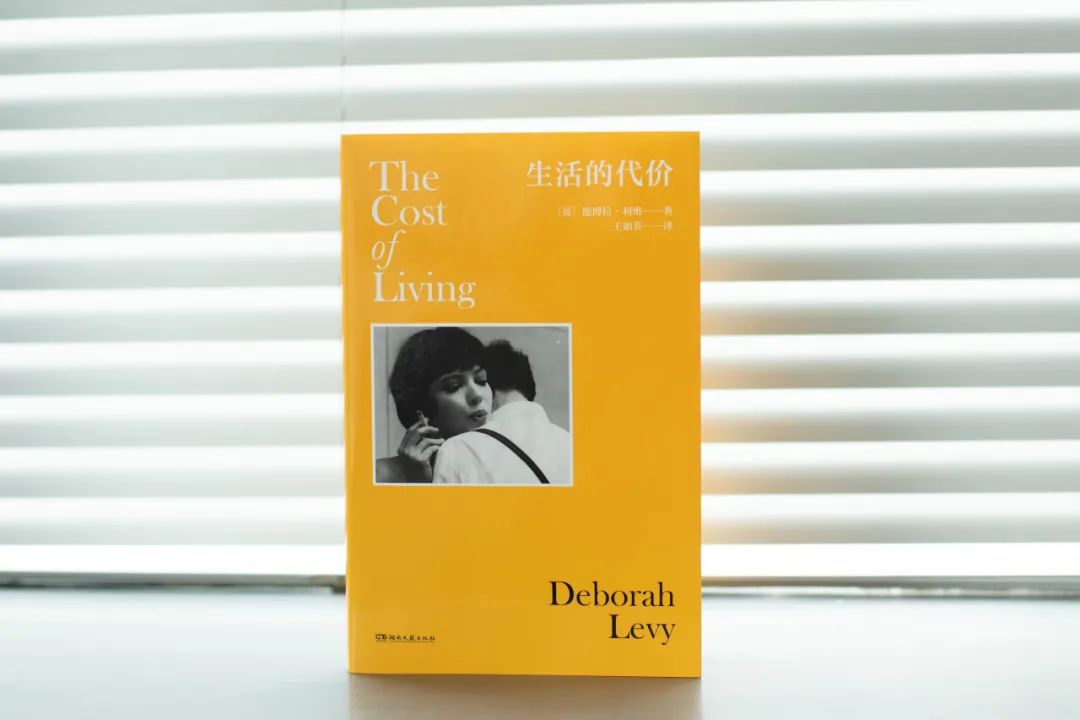
在奥地利的一个文学节上,我遇见了一位罗马尼亚作家,她1987 年流亡到了瑞士,在苏黎世的一条街上租了间房,那里很像她在布加勒斯特1 生活过的街道。她还把苏黎世的房间布置得跟她在布加勒斯特的房间大体一样。她提醒我,我二十九岁时写了一本名叫《吞下地理》的系列短篇集。其实我并没忘记自己写过这么一本书,但这书能让她耳目一新,这让我很高兴。她对我说,她曾把以下女性叙述者的旁白钉在她床边的墙上:
每一段新的旅程都是在哀悼遗失的过往。流浪者有时会试图在新的地方再造从前。
此刻,我似乎就是在忙着将这里还原成我从前写作间的模样。

新文化时期的婚姻现实和离婚状况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剧变中的社会规范如何影响不同背景的女性,而她们在变革的大潮中又如何自处
孔慧怡《五四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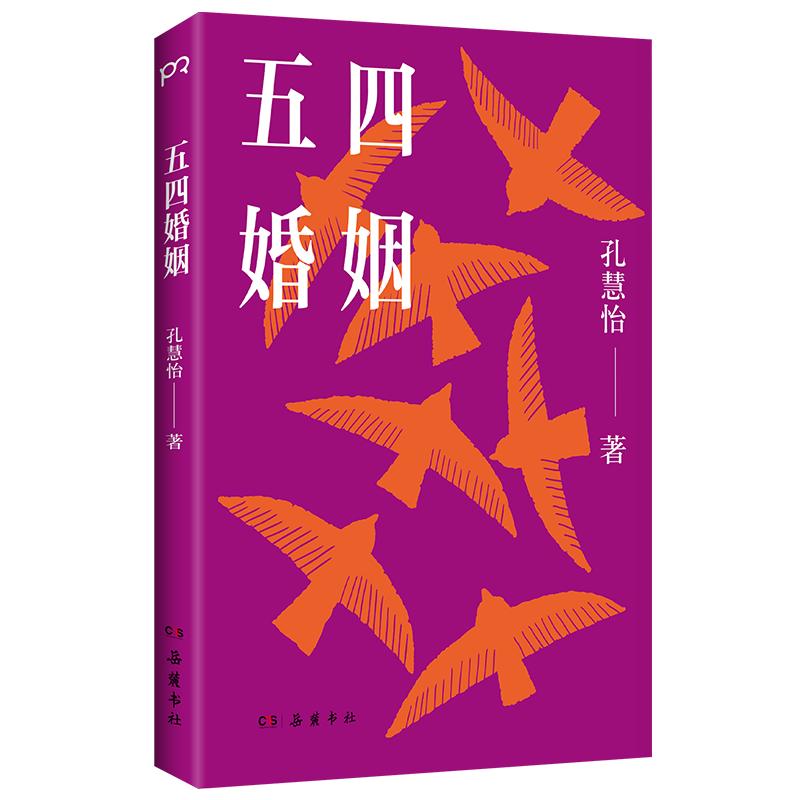

中国妇女运动的起源不在20世纪,而在19世纪;在妇女运动初始的二三十年,最卖力倡议和推动变革的不是女性,而是男人。
19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列强的威胁,有识之士不论在朝在野,都认定了自强乃救国之本,于是锐意维新;正是他们率先把“妇女问题”列入社会改革议程。但是当时在他们眼中,妇女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既没有主动性,也不是主体。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还大力批评说:“妇人干涉政治[指欧美妇女参政],在今日之社会,实利少而弊多。”由此可见维新时期的女性观发展到什么阶段。
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这三十年间,在中国以男性为主力推动的妇女运动有两大口号,第一是“反缠足”,第二是“兴女学”;前者为了提高女性的体能,后者则是提高女性的智能。当时不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男性都认为这是“强民”的基础。
改革者眼中的女性国民是潜在的社会资源,他们的目标是把这资源引进强国兴邦的大潮中;改革蓝图上的新女性占的位置可以用“贤妻良母”四个字概括。她们固然不能再像先辈那样身体孱弱,不受教育,但她们在体力和心智方面的发展仍然只是为了履行传统家庭中的角色,通过对家中男性的支持和培育,为增强国力作出贡献,因此当时另一个流行口号就是“国民之母”。
求变的种子落入中国思想界的土壤,生根发芽后就进入新阶段。当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有机会亲身接触西方社会模式,为中国新女性运动提供了参照的榜样。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胡适的观点如何因个人体验而改变,是个好的例子。他到美国留学以前,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为国人制造贤妻良母;到美国几年以后,观察西方社会的标准,目睹美国女性在社会上的位置,又与当地女性建立深厚的交谊,导致他的想法明显改变了,认为女子运动的最高标的应该是“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的女子”。
“自由独立”正是中国妇女运动第二浪的核心价值。20世纪10年代,女性角色划定于传统家庭结构这种想法受到挑战,而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也进入了激进阶段。这个新趋势与同时期酝酿的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新文化运动最关注的,是打破传统家庭尊卑长幼的运作模式,争取个人和个性解放。这个新潮流打造了另一种理想女性的形象,抛弃了配合传统家庭结构的“贤妻良母”观念,改为标榜五四新女性的“独立人格”。

原标题:《关于女性的一切可能:“走向更加自由的未来”》